时间: 2021-09-28 11:23
来源: 绿茵陈
作者: 王凯军
王凯军老师年少成名,在科研上卓有成就。特别是,他和中国第一代环保工作者一起工作,经历了中国环保重大事件的全过程。
去年值王凯军老师生日,在弟子们的一再要求下,他开始陆续回顾从业以来的经历和经验,在此基础上,口述了《环保回忆录》。绿茵陈和913工作室等一起,有幸记录整理相关内容。
本文截取了王老师在污泥和畜禽领域里续写的厌氧篇章、十万亿燃气工程出台的细节,内容涉及中持绿色的诞生与发展、污泥以及其他城乡有机废弃物处理的探索等。
通过几十年与企业和产业界的合作,我深刻认识到技术和产业推进中“天时、地利、人和”三因素的重要性。
“天时”很好理解,指技术所在领域恰得其时,大势将至,进入得太早或太晚都不行;“地利”是说企业必须占据一定的地域优势。简单理解,是看它在这个领域或区域有没有自己的优势;更深层次是看企业在特定领域有没有相关基因。比如UASB,我跟十多个单位合作过,最终只有十方一家做成了,就是因为它的基因优势;“人和”就和找对象一样,得看对了眼,有共同语言,人和人之间合作是一种双向选择。
谈到污泥与畜禽厌氧消化,很多人都认为我应该和十方公司合作,延续过去在工业厌氧领域成功的经验,十方虽然在工业领域非常成功,它却不一定具有在市政领域深耕的基因,就是没有“地利”。
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污泥厌氧这一历史使命注定要更换主角。
在我心目中,新登场的中持公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农村生物燃气领域的“天时”也不错,他们也有着跟县城及以下区域打交道的基因,但如果不认同这个理念,一样合作不了。
我与中持合作污泥厌氧处理的故事,开始于2008年的几个契机。
01污泥厌氧消化与中持绿色的起步
Anaerobic digestion of sludge and its industrializa
污泥问题由来已久,但行业里基本停留在坐而论道的阶段,没能真正推动厌氧消化工作。
为什么市政污泥领域的厌氧消化推不动?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掌握主流话语权的市政人比较保守,长期以来,他们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城市污水上。外面的工业废水及农业废弃物处理需求不断演化,厌氧技术在这些领域用得风生水起,但他们不太关注,也不够了解。
2008年,金源创始人许国栋二次创业,建立了中持品牌,业务聚焦在水务领域。同期,我给部委做“十二五”规划,提出污泥厌氧消化应该成为重点。这两件事在我脑海中碰出了一个火花,于是我给许国栋建议,在污泥领域可以成立一个公司,借此把污泥的厌氧消化搞起来。
虽然,后来我和许总一起做了许多事情,有很多交集。但是,在2008年之前我没有和他正式合作过。一个时期老许经常到北京环保所,他与环保所我前任总工王绍堂交往密切,但和我没有太多直接交往。

许国栋(左)与我
我和许国栋认识不算晚,他有几件事让我很难忘。
他初出茅庐时,就拒绝了台湾水美公司的橄榄枝。大概是1992年底左右,许国栋刚创业不久(他硕士毕业后在北京建工学院任职,受到十三大和小平南巡的感召,于92年下海,带着他的一帮学生创办了校办企业)。
这一时期,包括环保在内的各类产业都刚刚开始萌芽,文一波、赵笠钧等人也正不约而同地从体制内出来,准备施展身手。当时许总的公司体量还非常小,来大陆开拓市场的台湾省水美公司找到他,想谈谈入资或者收购他们作为平台。但是听说许国栋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并表示:“3年后,我们就是大陆的水美,并且规模会超过你们。”
此后,水美公司廖学贤董事长通过北京环保所总工沈光范先生(找许国栋也是他联络的)找到我,当时我正在荷兰攻读博士。水美廖总在荷兰鹿特丹定了一家高档餐馆,约我一起谈谈,并表示希望我加盟中国水美,和他们一起干。
我是如何回绝他的已经记不清了,但是肯定没有国栋兄的豪情。不过,他订了豪华餐馆请我吃牛排,仍然让我记忆犹新,那可能是我吃过的最高级的牛排,年代久远,滋味早已忘记,只记得价格是150荷兰盾一份。
水美公司最终与杭州纺织研究所的余淦生一起成立了杭州水美,也做成了几个大项目,初期效益很是不错。
90年代的企业家,眼界、心气、志向都很高。那个时代也为他们提供了绝佳的舞台,他们的前面一马平川,有大把的事情可想、可做。他们的目标很大、很清晰,且很可能真的做成。

知交酒友
当时不知道许国栋对我是什么感觉,但是,他对我所做的工作还是认可的。
90年代末,许国栋离开北京公司总部只身去了无锡办环保设备厂,呆了两年。期间有一回,他让我带着他去认识上海帕克公司的张巍,我们约在上海见面。
从帕克公司出来许总送我去机场,路上提出邀请我加盟金源。我说:“你的公司做得不错,但事太少了,没有我做的事。”我的意思是,在环保所我想研究什么,就可以研究什么,不受限制,而公司受主营业务限制。这件事可能给老许留下了错觉,很长时间他不和我合作,究其原因,说我“花心”,关于这一点,我们争论了好多年。
但是,很快我又找到他参加我们的九五攻关《UASB反应器设备化及其配套产品开发》产业化课题鉴定会。他很意外我请他作为专家,实际上我是请他了解厌氧,我们在寻求和他合作的机会。
在这次鉴定会上,我建议他与我们合作推动厌氧技术时,他有些犹疑,我劝说他:“不能因为和路雪厌氧项目,你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厌氧呀。”他听后吃了一惊:“连这你都知道?”但是,当时我们仍然没有合作成。
这次,在污泥问题上,我的想法与他一拍即合。我判断,要想把污泥厌氧真正做起来,需要把市政人的注意点吸引过来,让他们了解厌氧世界的精彩发展,拉他们一起上船。所以我给老许建议,将其他三位专家聚在一起,来探讨、推进这件事。
大家也建议通过住建部来推动污泥厌氧消化事业,并找到时任住建部城建司司长的张悦一起来推动。但是,那时候,住建部请国外咨询公司利用亚行项目对中国的污泥处理处置进行咨询,并且组织去欧洲考察,张悦因此选择推动水热预处理的高级厌氧技术,主要是康碧公司的技术。
许国栋对搞厌氧的思路很认可,他想把事情做成,对其他细节不太看重。就这样,中持绿色宣告成立。成立之初,是以我们四个专家为主设计中持绿色的结构,这个公司结构保持了多年,直到融资阶段才有所变动。当时许总想找投资,但对于投资人来说,这种股权结构太过分散,难以操作。大家就一起商议,都同意应该以中持为主。
因为中持绿色当时的业务主推是污泥,我又想起了我在2002年申请的一个技术专利——滚筒式动态污泥堆肥发酵设备,在卧式旋转发酵罐的基础上进行设计,经过生产能力计算和规模设计,实现动态发酵。
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我用这个设备在北京密云污水厂做过一个污泥堆肥的示范工程,效果不错,停留时间只需要7天(普通工艺需要20天),处理效率很高,产品配合建设了一个3万吨的复混肥厂。
生产的产品在我们设计的200亩大兴庞各庄污泥转运站进行了农业实验,当时是北京市科委支持的一个污泥堆肥项目,污泥堆肥效果好,污泥制品符合国家要求。我也是通过这个项目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应该说复混肥而不是复合肥,因为国家有复混肥的标准和产品,复合肥是俗称。
让我印象更深刻的是这样几个事实:
根据国家复混肥的标准,三组分(N+P+K)的比例要求,浓度不低于25%,产品绝大部分的成分仍然是化肥,污泥添加量低于10%,消纳不了多少污泥;另外,当时每个县都有一个以上的复混肥生产厂,大部分还吃不饱,污泥堆肥产品很难进入到他们的销售渠道。
这个项目之后,我就没有再继续进行堆肥的产业化推广。我想到滚筒设备很适合中持绿色的污泥业务,就开玩笑说:“这是达坂城的姑娘,嫁给你们一个温度分级生物分相的姐姐,还配上动态滚筒的妹妹,只要求你们推好了,记得我。”我把滚筒堆肥技术也无偿给了他们,听说他们现在已经推了10几套,邵凯还惦记着这个事情。
2021年9月25日,当本节内容第一次在微信里发表时,中持的凯叔(杨永凯)转发朋友圈并回忆说,2011年5月,在白鹭园市场培训会晚餐后,在我的房间里,听我给他们说动态滚筒的技术。当时我找出研究报告和ppt给了他们。没想到,当年9月份,中持就按照研究总结中的参数,做出了第一代中试的发酵滚筒。
那时我负责江苏省一个污泥技术研发和筛选项目,在无锡芦村污水处理厂做各种技术对比和评估。中持表示:“我们不要钱,自费来参加课题。”于是我帮他们安排,做了滚筒技术的小试、中试。
杨永凯回忆,2011年10月到年底,在无锡卢村污水厂做中试,那时候他同事刘彬才刚毕业。他们与我课题组常博士和汪博士一起。
2012年,在河北任丘又做了一年中试,2013年才使小滚筒摇身一变,变成了工程化的大滚筒。这才练就神器,才有中持在污泥、畜禽粪便、化粪池粪便、餐厨垃圾上十几个大应用。
杨永凯自己,毕业15年,其中用10年做好氧滚筒。
当然过程不是说起来几句话这么简单,我扶上马还送了一程。但其中的艰辛只有中持团队里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懂。
就这样,中持绿色聚集了第一波推动力。最开始的业务领域是污泥,主打工艺是分级分相厌氧消化技术和滚筒式动态污泥堆肥发酵设备。另一方面,中持还争取了一个国家863课题——城市污泥分级分相厌氧消化组合技术研发及工程示范项目,并在浙江宁海县成功应用。
中持绿色还有一项招牌工艺——加钙干化,主要针对一些地区爆发出的污泥污染问题,进行应急处理。特别是当时环保部出台了50%的污泥干化政策,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加钙干化需求。中持当时有很多机会,帮客户做过几个应急项目,效果都还不错。
为此邵凯和老许还发生了很大的争执。邵凯向老许汇报此事时,老许不同意继续发展这个业务,认为跟公司价值观和中持绿色战略不符。听中持员工讲,邵凯从许总办公室出来后,在楼道里大声讲:“以后再遇到挣钱的业务,一定不要和老许说。”
在此冲突之前,我十分赞成邵凯推动此项业务,有一次碰到他,还和他探讨,说这件事印证了德鲁克创新理论中七大创新机会之一,意外事件是创新的一个重要契机——突然爆发的需求,需要相应技术。我们一起上过德鲁克的课,在一起分享经验。
后来从战略投资商对公司的认同上,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许总的坚持是有道理的。由于中持绿色基因纯正,策略正确,很快得到许国栋基金朋友圈的认可,在中持绿色刚开始,投资商以上百倍的PE值投入6000多万元,是超成功融资。当然,这一切不能以成败论英雄,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在产业上的思考和探索,意义在于过程的丰富多彩,并不完全在于结果成败与否。
有了资金之后,有一次,许总和邵凯一起约我去杭州跟杭能谈收购的事情。杭能的蔡昌达一直从事沼气行业,我跟他比较熟,已经相识了一、二十年,他们请我充当中间人一起去谈。
在飞机上,我跟他们详细介绍、分析了杭能的基本状况,杭能与中持有相似的精品工程基因,老蔡做的项目是德国品质。
我经常说金源和金达莱(创始人廖志民)是上世纪环保行业里值得称道的两家公司,能把污水处理厂建设得与国外一个水平,碰巧两个公司的老总还是清华同窗。
我曾经看过老许他们做的几个污水厂,一走进去,给人的直观感受像进了国外的污水处理厂。那时,金源的客户群主要是外商和合资企业,掌握了外企的一整套方法、原则,内化成了自己的审美与标准,在工程上非常讲究施工的外形、结构。
他们的公司使命是许国栋提出来的:给中国人建好的污水处理厂。创业之初,正赶上国内需要建设大量污水厂,但多数工程都是非专业人士在做,质量参差不齐,他觉得有使命去做出好的污水厂。
金达莱廖志民也是非常注重细节,他们起步时在深圳、东莞做电镀废水,几种电镀废水,十几条管道布置得井井有条;车间都是用地板漆刷,一尘不染——去参观他们的车间后,我才知道什么是地板漆,以前没有见过。后来联合国维和部队都采购了金达莱的设备。

左二廖志民、右一许国栋
除了这俩,杭能是另一个能把工程做到极致的公司,只是它以前不属于环保圈。
我跟许总和邵总分析,杭能当时每年盈利大概是在一千多万,但是,它只做厌氧部分。所以,并购之后如果做整个工程EPC的话,合同额翻倍,利润可以上升到三千万以上。虽然,中持绿色当时盈利并不高,只有几百万。但是,在当时的时间节点,一两年以后应该能发展成三五千万利润的公司,所以合并对中持绿色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当时蔡昌达已经接近70岁了,他也想收山,所以我们去了以后谈了比较好的价格。但是回来以后,中持内部商量,收购没有进行下去。
两年后,维尔利以四点几亿的高价收购了杭能,这是国内环保界少有的几个成功并购,同时又实现企业文化很好融合的案例。与杭能合并助推了维尔利从垃圾渗滤液领域到有机固废处理的成功转型,现在维尔利在有机固废的厌氧处理技术上,成为行业翘楚。从这个角度说,中持放弃了收购机会,确实非常可惜。
02城乡有机废弃物处理:从“十万亿”到“三级网络”
Urban and rural organic waste treatment
《世界能源》展望到2030年,中国天然气需求量将会达到4000亿,缺口2000亿。 2030年,中国天然气需求量将从2012年的1816亿达到4000亿。当时我国天然气的产量是1500多亿,未来加上进口量,能到2000亿。还有将近2000亿的缺口,怎么办?
这个缺口可以通过煤制气+生物天然气两条途径来填补。当时我国在煤制气领域已经有所突破,在新疆还建有专门的能源基地,西气东输等工程也开始上马。煤制气1500亿后,还有500亿可以采用生物质燃气,这就需要与厌氧消化、餐厨垃圾、沼气等技术来结合,这是一个大战略。
为此,国家专门在科技部设立了一个生物天然气的专项,除了承担研究任务,还承接产业上的事情。围绕这个专项,开展了一系列的课题,给科技部提出了一个“100亿”的产业目标。
我们是搞厌氧出身的,这是我们的本业,总要提出一点想法,要有所作为,所以,我跟左剑恶教授一起商量和策划,从而产生了“十、万、亿” 计划的构思。
2013年底,通过老甘(甘海南)【相关链接:说服甘海南改行】,我约到了时任山东省环保厅领导,甘海南、左剑恶和我一起到省厅跟他汇报在山东实施“十万亿计划”的可行性。
我将国外的情况、技术的情况、山东的优势做了详细介绍。
具体的想法是配合污染治理和温室气体减排,在山东十余个地级市建设十个沼气生产基地,每个基地包括 十个生物质燃气项目,合起来有一百来个项目;在十个城市推动清洁能源汽车,每个城市推行千辆,合起来有万辆规模;为了缓解大气污染,在百万户农村提供生物天然气替代煤炭。最终达到 10 亿的生物燃气的产量。
我把这些计划中的数字合起来,变成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十万亿计划”。
我认为搞生物天然气条件已经具备且需求也都起来了。当时我们调研过很多国外案例,如瑞典有了沼气汽车,甚至还有沼气能源的火车;德国真正把能源作物和沼气做成了产业,可再生能源处于世界领先。
从山东当时的情况来看,在资源、工程和技术上都有优势。山东是最早上清洁汽车的,十方厌氧技术也已经做了很多工程。食品行业已经初步具备基础,600多个食品加工厂产沼气可以达到10亿方。餐厨垃圾产生的填埋气可以达到2亿方,从沼气潜力上看,山东省食品行业全国排第一,农业全国排在第二,畜禽养殖和秸秆有20亿方的沼气生产潜力。
我认为如果开展生物天然气工作,还能够有效缓解山东的大气污染。
当时山东全省耗煤2.4亿,农村的散煤用量约有4000万,这些散煤燃烧均未经处理就排放到了大气中,产生的污染量是热电厂的10倍以上。且这些散煤主要集中在冬季的4个月取暖,导致冬天的污染物排放强度又增加了3倍。
因此,在“十万亿计划”中提出给百万户农民提供生物天然气替代散煤取暖,这样散煤污染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
听完后,大家对这些内容非常感兴趣,包括我提到的大气污染治理思路,和畜禽养殖废弃物的再利用。
但当时各地环保厅全副精力都放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时间、任务都很紧迫,暂时腾不出空来。所以,山东省决定半年或一年后,等把大气污染治理的思路理清了、工作捋顺了,再详细商讨这件事。
当时,我们与中国水网配合,与山东省环保厅在济南主办了“山东省生物质高质利用技术论坛暨试点工作对接交流会”,探讨了山东省生物质高质利用的现状及产业发展前景。
会上,我借机提出山东省“十、万、亿”燃气项目倡议:可以优化产业布局,改善能源结构,缓解大气污染,支撑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战略。
山东省环保厅研发中心主任李保林明确表示:“举办论坛为供需双方搭建了平台,有利于推进日后合作。对于启动的试点工程,省里会给予支持,省环保厅也会为生物质高质利用提供支持”。
这段时间,有一次郝吉明院士刚好也在济南参与治理大气污染的相关工作,我们就拉了郝院士一起约着和济南市市长谈。
那天等了很长时间,后来一个市委常委出来见我们,说有领导到济南,书记、市长去接待,无法参加。回到北京我们才知道是赶上领导人来济南。说完事吃完饭,我和左老师火车都赶不上了。因为第二天我们在北京都有会议,十方的人连夜开车把我们送回来,到北京都凌晨三、四点钟了。
当时,我想起和左剑恶老师另一个有意思的出差场景。
“十一五”水专项初期,我刚准备调到清华,水专项的分配都已经基本完成,那时候我和左老师在水专项里头的方向不甚明确,我们商量在污泥厌氧消化上做点儿工作,打听到唯一没有确定的项目是昆明的城市水专项。
2008年五一过后,我和左老师就相约去到云南,与云南省厅、省院主管水专项的人都见了面,谈了一圈儿,效果不甚理想。
5月12日,我们将要离开昆明回到北京。我们在路上坐着出租车,突然感到有一阵晃动,左老师比较敏感,说“有地震”,我当时没有在意。
我和左老师还想按计划回北京,但是到机场之后发现形势不对。听说军用飞机大量集结,我和左老师果断换上前一班的飞机回京,到了北京才知道四川汶川发生了大地震,如果当时我们没有换飞机,估计一个星期也回不了北京。
我跟左老师出差,确实有不断的历险,都是值得记忆的事儿。
一年以后,环保厅争取到省里的相关资金,计划做三件事。
第一件是支持山东省环境规划院做一个三级网络的研究,同时,支持了两个项目。
一个是肥城项目,另一个是济南周边的项目,后来济南周边那个项目由于一年都没动工,资金被收回了。肥城那个项目颇费周折,但最终完满落地,我将在后面详细提到。
03“三级网络”的缘起
The origin of "three-level network"
山东省环保厅找到我,没有直接提“十、万、亿”燃气项目的事情,而是提出“三级网络”新理念,也跟厅领导的情怀和接地气的特点息息相关。他首先给我们讲了他和老农的一场对话的感受。
有一次,他去水库边上考察,遇上一个老农民,老人家里养了几口猪,两个儿子到外地上大学,也是靠着每年养猪的钱支持。然而这几年,因为环保问题,水库周边政府新政策不让养猪了。
老农委屈地说:环保你们才搞了几年,我祖祖辈辈都在这里住,咋就不让养了?不养猪我怎么生活?
和老农的对话,对他触动很大,于是就开始考虑畜禽污染问题的解决,要解决散养户的环保问题,需要找到既可以解决畜禽污染问题又不影响农民生活的路径。解决问题需要顶层设计,通过三级网络系统可以解决这一系统问题。
我们一拍即合,还据此跟山东省环科院一起做了个顶层设计规划。
所谓三级网络,就是以全县域为服务单元,建立收集、转化和利用三级网络体系,对全县有机废弃物进行协同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综合解决区域内有机废弃物的污染问题,生产生物天然气和有机肥等资源化产品。
我们提出,第一级网络由政府主导制定政策,建立污染物收集、储存和运输的体系,政府参与对收储运模式进行优化创新;第二级网络由企业主导,建立污染物处理和资源化转化系统;第三级网络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推动,进行资源化产品销售与利用模式的探索。
前面说到,山东省三级网络要搞两个试点项目,济南周边还有一个项目,当时由于示范工程不落实,第一笔2000多万经费被收回了。
另外一个项目选了肥城,山东十方承担了肥城项目。当时甘海南在推餐厨垃圾,餐厨有许多技术和商业模式问题没解决,没有投入主要精力到三级网络的试点项目。注册了一个公司后,没有实质性推动,所以就有些停滞。
在一次著名的餐厨领域人聚会后,我和邵凯从青岛返回。在机场,我告诉他,中持绿色参与的产业化研究课题遇到一些困难,在项目示范工程方面也不太顺利。另外,十方现在投资投不动,并且三级网络没有算过账来,觉得挣不了钱,持怀疑态度。
所以,我希望邵凯能够帮助探讨收购肥城项目,这样既救活了产业化项目,同时又帮助了三级网络落地。

中持和十方探讨合作
邵总爽快地说这个事他来办,这是我第二次和邵总成功合作推动项目实施。他回去以后,李彩斌马上跟十方对接,很快就达成了协议,接手这个项目,中持绿色控股90%,十方保留10%股份。
邵凯的强大执行力,我一直是十分欣赏的。我常说邵总是我和中持合作的福将。
合作是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的,我和许总是君子和而不同。而跟邵凯,却是一见如故,一拍即合。我们一起推了三次合作,都很愉快。
一是在污泥领域的第一次合作。前面说过在我的建议下,为了开拓污泥领域市场,老许成立了中持绿色。我向他推荐邵凯来做总经理,老许也说我是慧眼识英雄。在邵凯带领下,中持绿色有声有色地做了起来,完成了污泥温度分级生物分相技术。
二是适时推动了污泥滚筒动态堆肥和石灰干化技术。
第三个就是三级网络肥城项目的落地。三级网络虽然现在还没有在全国推广起来,但是,对于中持来说,借着肥城项目厌氧干发酵技术,顺利推进了“十二五”水专项的任务完成。以此为契机,推进了很多项目。
后来的睢县和宜兴的城市污水处理概念厂、与三峡合作等,都有厌氧干发酵技术的影子。甚至,老许的工程博士论文也跟它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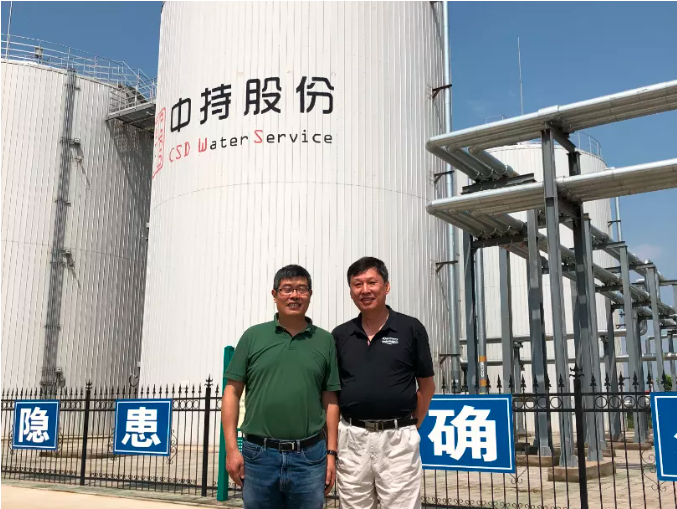
与李彩斌(左)在秦皇岛项目
肥城项目的建设过程,我没有太多参与,建完之后去看了一下确实出乎意料,这个项目有几个方面可圈可点。
第一是开发了大型干式厌氧反应器,一次放大到3000方。
国外的干式厌氧反应器由于搅拌器放大问题,一般就做到500方,最大能到2000多方。做到3000立方米在技术和设备上一定有重大突破,这显示制造技术水平的提升。
所以,我跟许总说,你们的团队在大型设备制造上有一些长处和诀窍,在滚筒堆肥等几个大型设备转化方面都做得非常好,这次,又是大型的卧式干式厌氧搅拌推动设备有所突破。
第二是在模式上有创新,确实体现了物料多样性,也表现在县级综合治理上的探索,从各家各户收集的畜禽粪便,还收集预处理一部分秸秆,以及一部分餐厨,是一个有机固废综合性的处理设施。
第三确实体现了三级网络的基础网络特性,建立收储运网络,后续还有土地流转和肥料利用网络。

几个团队一起在肥城
出差肥城的搞笑故事
我们课题组、山东十方和中持三个团队一起去肥城项目现场参观,后来的路上摆了一个大乌龙。
由于现场讨论热烈,主人热情,到机场和高铁站都是以分秒控制——我一般到外地都会遇到这种情形。事实上,经常造成客人赶交通工具时狼狈不堪。
所以,那次也导致我们回来差点误了火车。我看见我的学生秋琳他们领着一大群人,匆匆忙忙拉着箱子,拎着肥城桃,追着火车跑,他们刚跳上去,车就发动了。但是,他们和我坐的不是一个方向的车,我感到奇怪,难道他们背着我有什么安排?
还没有回过神来,一个学生气喘吁吁打电话来,还忍不住笑。我心想:还好没有把老大忘了,还知道跟我说一声他们的秘密安排。让我啼笑皆非的是听到电话里说:老师您上错车了。
此刻,淡定坐在回京高铁上的我看了一下车票,笑着反问了一句:是你们上错车了吧。
他们上了反方向的车,去往上海方向,离北京越来越远……
厅领导对“环保+农业+能源”理念的落地情况非常重视,针对项目进展和推进思路开过好几次会。
但在项目落地未半之际,他任职有了变动,调入环境保护部。
在去北京的前一天,他还把环保厅、肥城、齐河县委书记等一行人叫到一起开了次会,商量两个项目下一步如何推进。那次会议我也参加了,很受感动。
会上讨论了两个项目,一是肥城项目,主攻畜禽污染物治理与综合利用;另一个是齐河县有机废弃物综合处理项目,打算把沼液和农业结合起来。

肥城市畜禽污染物治理与综合利用项目现场图
时至今日,中持绿色自己总结这些进展说:两代厌氧技术,共创低碳标杆。
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公示了《2021年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及示范工程名录(第一批,城镇污水处理低碳示范工程领域)》,由中持绿色提供污泥分级分相厌氧处理技术的宁海县城北污水处理厂和雎县第三污水处理厂的厌氧干发酵技术均入选。两个项目代表着两代厌氧技术历经十年的迭代与创新,为城镇污水处理厂的低碳发展,提供了先驱示范。
污水处理的目标不仅仅只是缓解污染问题,更应是综合考虑,从而回收能源和资源。厌氧技术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无疑已成为最重要的生物质能利用技术之一,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技术。所以在低碳时代来临的时刻,中持绿色十余年的探索和实践显示出其重要意义。
中持绿色三大技术利器(DANAS®干式厌氧发酵技术:突破传统厌氧技术的局限;SG-DACT®滚筒动态好氧高温发酵处理技术:应用场景多、领域广泛;ContiFerm®超深槽式连续好氧发酵技术:高效资源化处理及利用)成为公司发展的法宝,但更重要、更可贵的是在此基础上,他们的团队从技术到模式,沿着城乡循环方向,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进行不懈的探索。【相关链接:李彩斌:减污+降碳!中持绿色为环保与农业架起桥梁】
04君子之诺,重于泰山
The promise of gentlemen
几年后,我们这波人在农业项目上终于取得了一些进展:肥城项目顺利运行,十方那边的“沼液+农业”的项目也很顺利,试验的大米也成功种了出来。我们就商量,得跟原来的厅领导再汇报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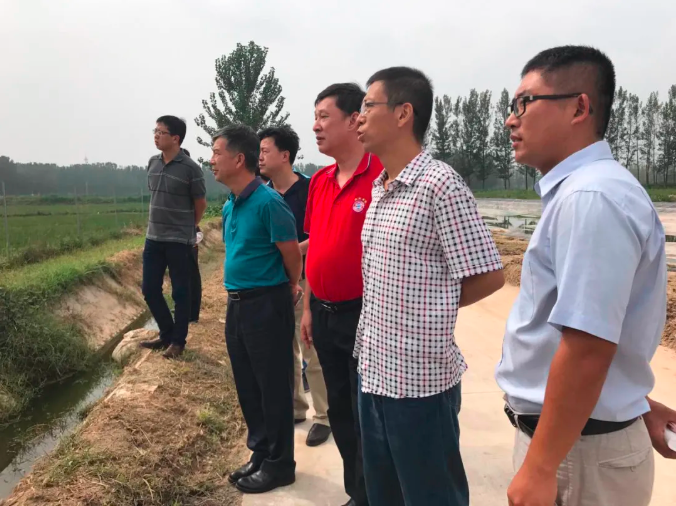
十方流转了1200亩土地种植黄河大米,我和左老师等去看现场
当时,他正在党校学习,找了个周末,安排在党校外头的宾馆里和我们见面。我叫上参与项目的李彩斌和甘海南等人,以及齐河和肥城的地方领导。老许也特意赶来参会。甘海南讲了土地流转消纳沼渣沼液培育黄河大米品牌,中持胡芳讲了肥城三级网络示范项目,我的学生边潇讲了三级网络的顶层规划——边潇的父母是厅领导在山东的老同事、老部下,她来介绍具有特殊意义,表示了我们的事业传承。
为了充分汇报齐河项目,十方甘总还把他们种出来的大米背了一袋过来,一边介绍一边现场煲了一锅饭,汇报结束饭也做好了,大家分而食之,边吃边聊。
经过这几年的探索和实践,我们从聚焦处理设施,逐渐转移到基于建立全域覆盖与区域统筹相结合的城乡有机废弃物区域解决方案,理念包含了收运处理模式以及城乡有机废弃物全过程、全生命周期的统筹管理,即以全县域为服务单元,建立“收储运、转化和利用”三级网络体系,综合解决区域内有机废弃物的污染问题,生产生物天然气和有机肥等资源化产品。我们三级网络形成了县域的绿色生态基础设施,这样将边界进行外延和拓展。
我主持汇报会议时说,这次会议是君子之约,几年之前大家商定的一件事。虽然现在厅领导已经不管山东这摊事儿了,但君子一诺要有结果,我们在做得差不多的时候,过来做一个交代。
领导听完后说:可惜了,可惜了。他说的可惜之一,是环保部主管的部门和人应该来,但是临时有事,没有参加;可惜之二,是觉得应该把同在党校学习的农业部的领导叫上,一块听听这个思路。
后来肥城项目也得到了农业部、环境部的认可,被挂上了诸多试点牌子。
中国人有重诺的传统,这段故事,可以说也是一段君子之诺的佳话了。
编辑: 赵凡
